| [1] |
[美]米尔顿·弗里德曼. 资本主义与自由[M]. 张瑞玉,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9, 4.
|
| [2] |
TOLLES F B, CREMIN L A. American Education: The Colonial Experience 1607-1783[M]. New York: Harper & Row. Publishers, Inc, 1970.
|
| [3] |
[美]劳伦斯A. 克雷明. 美国教育史——建国初期的历程(1783-1876)[M]. 洪成文, 丁邦平, 刘建永, 等译.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2.
|
| [4] |
林玉体. 西洋教育史专题研究论文集[G]. 台北: 文景出版社, 1984.
|
| [5] |
[美]韦恩·厄本, 杰宁斯·瓦格纳. 美国教育: 一部历史档案[M]. 周晟, 谢爱磊, 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9.
|
| [6] |
陈学飞. 美国高等教育发展史[M]. 成都: 四川大学出版社, 1989.
|
| [7] |
MCPHERSON M S, WILSON J T. Academic Science, Higher Education, and the Federal Government, 1950-1983[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3.
|
| [8] |
[美]亚历山大·里帕. 自由社会中的教育[M]. 於荣, 译. 合肥: 安徽教育出版社, 2010.
|
| [9] |
滕大春. 美国教育史[M].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 2001.
|
| [10] |
[美]麦克斯·J·斯基德摩, 马歇尔·卡特·特里普. 美国政府简介[M]. 北京: 中国经济出版社, 1993.
|
| [11] |
[美]詹姆斯·M. 伯恩斯, 等. 民治政府[M]. 陆震纶, 郑明哲, 等译.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6.
|
| [12] |
[美]理查德·D·范斯科德, 理查德·J·克拉夫特, 约翰·D·哈斯, 合著. 美国教育基础——社会展望[M]. 北京师范大学外国教育研究所, 译. 北京: 教育科学出版社, 1984.
|
| [13] |
[英]罗素. 权力论: 新社会分析[M]. 吴有三,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8.
|
| [14] |
[英]罗德里克·马丁. 权力社会学[M]. 丰子义、张宁, 译. 北京: 三联书店出版社, 1992.
|
| [15] |
[美]汉斯·摩根索. 国家间政治——权力斗争与和平[M]. 徐昕, 等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
| [16] |
[英]安东尼·吉登斯. 民族-国家与暴力[M]. 胡宗泽、赵力涛, 译. 北京: 三联书店, 1998.
|
| [17] |
[英]弗里德里希·哈耶克. 自由宪章[M]. 杨玉生、冯兴元、陈茅, 译.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8: 195.
|
| [18] |
PUSEYNATHAN M. American Higher Education: 1945-1970[M].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8: 111-112.
|
| [19] |
谢文全. 比较教育行政[M]. 台北: 五南图书出版公司, 1996.
|
| [20] |
[美]梅里亚姆. 美国政治学说史[M]. 朱曾汶,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8.
|
| [21] |
[汉]郑玄, 著. [唐]孔颖达, 疏. 《礼记正义》[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9.
|
| [22] |
SHAVELSON R J, TOWNE L. Scientific Research in Education[M]. Washington DC: National Academy Press, 2002.
|
| [23] |
[美]汉密尔顿, 杰伊, 麦迪逊, 等. 联邦党人文集[M]. 程逢如, 等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0.
|
| [24] |
CUBBERLEY E P. Public Educ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M].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1947.
|
| [25] |
CHRISTOPHER J, DAVID R. The Academic Revolution[M]. New Brunswick: Transaction Publishers, 2001.
|
| [26] |
JOHN S B, WILLS R. Higher Education in Transition—A History of America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M]. New Brunswick. Transaction Publishers, 1976.
|
| [27] |
滕大春. 美国教育史[M].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 2001.
|

 点击查看大图
点击查看大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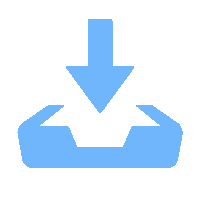 下载:
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