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Rational Dimension of Social Practice Education
-
摘要: 社会实践教育是以社会为教育背景,藉由社会实践平台培养价值观、提升综合素质的教育活动,实践性和教育性是其根本特质。理性内在于社会实践教育之中,社会实践教育经由理性而达成。理论认识不足、忽视基于内感知的心理经验、缺少基于过程体验的价值引导,是社会实践教育中理性阙如的主要表现。彰显社会实践教育的理性之维,整合社会实践教育的实践性和教育性,需要着眼于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增进实践之知、加强社会实践中的价值引导、促成实践反思等方面。Abstract: Social practice education is an educational activity that takes society as its background, which cultivates values through social platforms, and enhances comprehensive qualities. Its fundamental characteristics are its practicality and educational nature. Rationality is inherent in social practice education that is achieved through rationality. However, the absence of rationality in the realm of social practice education is manifested by inadequate theoretical comprehension, disregard for psychological experiences rooted in internal perception, and a dearth of value guidance based on experiential processes. To demonstrate the rational dimension of social practice education and integrate its practicality and educational nature, it is imperative to respect the leading status of students, foster cognitive of value and knowledge through practical engagement, reinforce value guidance within social practice, and facilitate introspective contemplation.
-
Key words:
- Social practice /
- Social practice education /
- Rationality
-
[1] 张汝伦. 历史与实践[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5. [2] 丁立群. 技术实践论: 另一种实践哲学传统——弗兰西斯·培根的实践哲学[J]. 江海学刊, 2006(4): 26-30. [3]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一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2. [4] 汉娜·阿伦特. 人的境况[M]. 王寅丽, 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7. [5] 杨国荣. 人类行动与实践智慧[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3. [6] 成尚荣. 实践育人的理论基础、核心要义与基本形态[J]. 中国教育学刊, 2022(10): 55-60. [7] 郑航. 和谐社会的"好生活"与道德理性的生长[J].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 2006(2): 27-33. [8] 杨国荣. 实践哲学: 视域与进路[J]. 学术月刊, 2013, 45(5): 39-51. [9] HIRST P. The demands of moral education: reason, virtues and practices[M]// HALSTEAD J, MCLAUGHLIN T. Education in morality. London: Routledge, 1999: 112. [10] 刘森林. 实践的逻辑[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9: 168 [11] HIRST P. Education, knowledge and practices[M]// BARROW R, WHITE P. Beyond liberal education: essays in honour of Paul H. Hirst. London: Routledge, 1993: 184-199. [12] 亚里士多德. 尼各马可伦理学[M]. 苗力田, 译.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9: 33. [13] 杜威. 道德教育原理[M]. 王承绪, 译. 杭州: 浙江教育出版社, 2003. [14] 阿尔弗雷德·诺斯·怀特海. 教育的目的[M]. 靳玉乐、刘富利, 译. 北京: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2019: 18. [15] 郭元祥. 论实践教育[J]. 课程·教材·教法, 2012, 32(1): 17-22. -

 点击查看大图
点击查看大图
计量
- 文章访问数: 1028
- HTML全文浏览量: 644
- PDF下载量: 466
- 被引次数: 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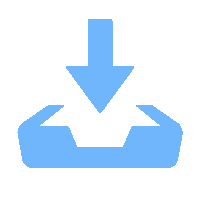 下载:
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