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n Chen Guisheng's Explorations in the Concept of Education
-
摘要: 陈桂生一贯重视教育学基本概念研究。他对教育概念的探讨典型地体现了概念研究的特点。文章回顾了他对“教育”一词的名实辨析,对教育概念与教育观念关系的澄清,对教育概念内涵演变的考察,发现他在教育概念定性上的摇摆妨碍其区分教育与教-学活动。近年来,在彼得斯工作的启发下,他从教育作为一种不可替代的价值的定性出发,展开了一系列关于教育学的反思,这使他将教育概念置于同教养、教-学活动概念的关系中进行考察。在澄清这些基本概念关系的基础上,他勾勒了教育学逻辑范畴的轮廓,提供了一幅理解教育学思考教育问题的概念地图,超越了对教育概念本身的探讨。在此过程中,他不仅察觉到欧陆教育学与英语地区教育学在理解教育价值方面的异同,而且通过教育文化比较洞悉了中西方教育文化的个性,甚至从中萌生了对本土教育文化的自信。Abstract: Chen Guisheng has always paid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study of basic concepts in pedagogy. His exploration of the concept of education typically prepresent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his conceptual research. His work is closely reviewed in this article including his analysis of the name and reality of the word "education", clarifying the link between the concept and the idea of education, and the examination of the evolution of the intension of education as a concept. It is found that his hesitation in the quality of the concept of education hinders his distinction between education and teaching-learning activities. In recent years, inspired by Peters' work, he has launched a series of reflections on pedagog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ducation as an irreplaceable value, which makes him examine the concept of education in the relationship with the concept of Buildung and teaching-learning activities. On the basis of clarify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se basic concepts, he framed the logical category of pedagogy, provided a conceptual map to understand education issues in one way only belonging to pedagogy, and went beyond the discussion of the concept of education itself. In this process, he not only perceived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in understanding education as one value between European pedagogy and English-speaking pedagogy, but also gained insight into the individuality of Chinese and Western education culture through the comparison of education culture, and even sprouted confidence in chinese local education culture.
-
Key words:
- Chen Guisheng /
- Concept of Education /
- Pedagogy
-
表 1 教育内涵“善”之两次转义
第一义 本义:个人之“善” 第二义 第一义的转义:个人的“完善” 第三义 第二义的转义:社会人的“完善” -
[1] 陈桂生. 教育原理[M]. 长沙: 湖南教育出版社, 1993. [2] 陈桂生. 教育学究竟是怎么一回事?[M].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2020. [3] 陈桂生. 教育学的建构[M]. 长沙: 湖南教育出版社, 1998. [4] 陈桂生. "教育学"视界辨析[M].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7. [5] 刘幸, 施克灿. "Education"何以译为"教育"——以日本有关学术史料为基础的讨论[J]. 教育研究, 2021(11): 86-95. https://www.cnki.com.cn/Article/CJFDTOTAL-JYYJ202111008.htm [6] 陈桂生. 常用教育概念辨析[M].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9. [7] 约翰·怀特. 再论教育目的[M]. 李永宏, 译. 北京: 教育科学出版社, 1997: 4. [8] 陈桂生. 教育原理[M].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0. [9] 陈桂生. 学校教育原理[M].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0. [10] 陈桂生. 普通教育学纲要[M].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9. [11] 陈桂生. 历史的"教育学现象"透视[M].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 1998. [12] 陈桂生. 教育学究竟是怎么一回事——略议教育学的基本概念[J]. 教育学报, 2018(1) : 3-12. https://www.cnki.com.cn/Article/CJFDTOTAL-XKJY201801001.htm [1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七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59: 400. -

 点击查看大图
点击查看大图
表(1)
计量
- 文章访问数: 2676
- HTML全文浏览量: 384
- PDF下载量: 131
- 被引次数: 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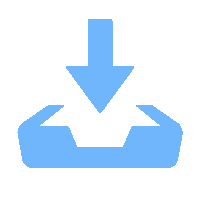 下载:
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