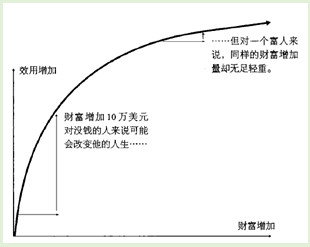| [1] |
亚当·斯密. 国富论[M], 唐日松等, 译.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05.
|
| [2] |
赫伯特·西蒙. 管理行为: 管理组织决策过程的研究[M], 杨砾、韩春立、徐立, 译, 北京: 北京经济出版社, 1988.
|
| [3] |
理查德·泰勒. "错误"的行为: 行为经济学关于世界的思考, 从个人到商业和社会[M], 王晋, 译.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16.
|
| [4] |
丹·艾瑞里, 怪诞行为学[M], 赵德亮、夏蓓洁, 译.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08.
|
| [5] |
丹尼尔·卡尼曼著. 思考, 快与慢[M]. 胡晓姣、李爱民、何梦莹, 译.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12.
|
| [6] |
William Samuelson & Richard Zeckhauser. Status quo bias in decision making, Journal of Risk and Uncertainty, 1988, volume 1, 7-59.
|
| [7] |
Fryer, R. G., Jr., Levitt, S. D., List, J., Sadoff, S., &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Enhancing the Efficacy of Teacher Incentives through Loss Aversion: A Field Experiment[R].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2012: . No. 18237.
|
| [8] |
托德·罗斯: 平均的终结: 如何在崇尚标准化的世界中胜出[M]. 梁本彬, 张秘, 译.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17.
|
| [9] |
Boylan, M., Wolstenholme, C., Maxwell, B., Jay, T., Stevens, A., & Demack, S. (2016). Longitudinal evaluation of the Mathematics Teacher Exchange: China-England. Interim research report. Retrieved from https://assets.publishing.service.gov.uk/government/uploads/system/uploads/attachment_data/file/536003/Mathematics_Teacher_Exchange_Interim_Report_FINAL_040716.pdf
|
| [10] |
Bloom, Madaus & Hastings, Evaluation to Improve Learning, New York: McGraw-Hill, 1981.
|
| [11] |
Benjamin S. Bloom. "Time and Learning", American Psychologist, 1974, 29(9): 682-688.
|
| [12] |
Benjamin S. Bloom, Human Characteristics and School Learning, New York: McGraw-Hill, 1976.
|
| [13] |
理查德·泰勒, 赢者的诅咒: 经济生活中的悖论与反常现象[M], 陈宇峰、曲亮, 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7.
|
| [14] |
理查德·泰勒、卡斯·桑斯坦. 助推: 事关健康、财富与快乐的最佳选择[M], 刘宁, 译.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09.
|
| [15] |
乔治·阿克洛夫、罗伯特·席勒著. 钓愚: 操纵与欺骗的经济学[M]. 张军, 译.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16.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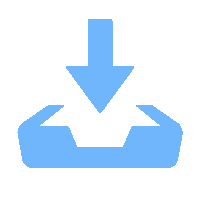 下载:
下载: